燒窯(散文)——?jiǎng)⒘⒂?/h1>
燒窯
劉立勇
稻谷入倉(cāng),紅薯落窖,秋的頭一拱,天氣就涼了。
稻草垛立在空蕩蕩的田野中,安靜、閑適。父親坐門(mén)檻上掏出火鐮,點(diǎn)燃老旱煙,仰望蒼穹下莽莽的九龍山。九龍山像九條騰躍的龍,尾擺頭揚(yáng)。此刻,它也像父親翻滾的心事,澎湃不已。父親正思慮把小炭窯擴(kuò)建成一窯產(chǎn)一千斤的大窯。你想,燒一窯炭大概需要一個(gè)星期,倘若一窯有一千斤,整個(gè)冬季的收入就可觀了。
天剛蒙蒙亮,我們還在賴(lài)床,父親起了床,帶著汪汪叫了幾聲的黃狗,沒(méi)入了林子。林子里很快響起父親高亢的山歌。喜鵲和斑鳩撲棱棱竄出樹(shù)蔭。
在這座山里,山下和山腰都是高大茂盛的杉樹(shù)松樹(shù),就山頂一圈兒,全是矮實(shí)的雜木,譬如櫸木、黃楊、柞樹(shù)、楸木、野栗子樹(shù)……這些樹(shù)木在山頂生長(zhǎng)十年、二十年,還是那么大個(gè)兒,根本無(wú)法看出它們的真實(shí)年輪。只有透過(guò)細(xì)密的紋理、褐亮的樹(shù)皮,方能感知它們?cè)陲L(fēng)雪里不屈的磨礪。
山里,每天都是這樣,早晨,太陽(yáng)最先給山頂抹上一層金黃,蒼老的樹(shù)皮上反射著煦暖的光芒,格外耀眼。然后光暈漸漸浸潤(rùn)山腰、山腳。太陽(yáng)落到山澗時(shí),差不多正午了。要是冬天,雪帽兒也最先覆蓋住這些堅(jiān)硬的雜木。
父親差不多和太陽(yáng)同時(shí)爬到山巔。父親朝手心哈一口熱氣,再使勁搓搓,又嚎幾句滾板調(diào)。山底下的木屋飄起裊裊炊煙。那樣苦難的日子,我從沒(méi)見(jiàn)過(guò)父親有半點(diǎn)頹廢。父親是我心中的標(biāo)桿,也像山頂巖壁上最堅(jiān)硬的一棵雜木。
炭窯建在當(dāng)陽(yáng)的風(fēng)口最好。當(dāng)風(fēng),火燃得更旺。而且最好能遠(yuǎn)遠(yuǎn)望得見(jiàn)家。那是母親的意思。盡管母親看不到父親貓窯里裝窯、出窯,但她可以看到窯頂?shù)臒煛8G頂冒濃黑煙時(shí),就知道父親燒窯了;煙豎得筆直時(shí),就是窯火燃旺了;像水墨畫(huà)一樣淡了、散了,就是該封窯了;天空干凈得只看到藍(lán)柔柔的底時(shí),就可以出窯了。
母親沒(méi)上過(guò)山,但母親喜歡遠(yuǎn)遠(yuǎn)地看山上的煙。
父親的炭窯比別人筑得精致。整個(gè)外形像個(gè)隆起的蒙古包。最外層涂抹的黃泥,父親用細(xì)篩過(guò)濾了一遍又一遍,光滑細(xì)膩。窯口方正的大麻石,還是父親從澗底挑上來(lái)的,砌得工工整整,出窯裝窯極為方便。四根粗壯的松木支撐杉木皮棚頂,就煙囪孤零零地插向天空。一千斤的炭窯顯得好敞闊,父親在炭窯里美美地躺了一袋煙的功夫。
砌好窯就可以正式燒炭了。先砍伐雜木。父親戴著耷耳帽,像只啄木鳥(niǎo),邦邦邦,木屑飛濺。雜木紋理細(xì)密堅(jiān)硬,碰到碗口粗的還需要斧子。嘩啦砍倒,削了細(xì)枝和樹(shù)葉,光木頭滾到窯旁的空坪,堆成小山。再下來(lái)用斧頭斫成短木段。父親的手法真好,好像每一截都精準(zhǔn)測(cè)量了一般,都剛好斫成一米長(zhǎng),在窯旁碼得整整齊齊。斫木頭時(shí)父親會(huì)將破棉襖甩得遠(yuǎn)遠(yuǎn)的,也不戴耷耳帽,哪怕下雪冰凍天,父親的頭頂都會(huì)直冒熱氣。父親一天要磨兩次砍刀和斧子。手掌虎口都震裂了,用膠布纏了一層又一層。雜木林偶爾也生出數(shù)根杉木、松木。但父親是不用杉木、松木燒炭的。那屬于泡木,泡木燒炭不亮火。雜木燒出的炭才易燃、耐燒,而且一燃熱氣就蹭蹭地上身。像櫸木炭、楸木炭、寡木子炭,還會(huì)發(fā)出歡快的啪啪聲,火星濺到褲腰上。
看著夠一窯的雜木就裝窯了。裝窯時(shí)還得有個(gè)好幫手。所以父親選擇我們放學(xué)時(shí)裝窯。父親弓著身子在窯里,我們負(fù)責(zé)將木頭搬運(yùn)到窯口。裝窯也有技巧,一般將小一些的雜木放外圍,粗壯的放中間,要擠得嚴(yán)嚴(yán)實(shí)實(shí),木炭才不會(huì)燒透。木頭也不能插入泥土,插入泥土就有煙腳。
封好窯,父親才可以歇口氣。然后在窯口燃起大火。山下的母親一抬頭就知道父親燒窯了。父親得很晚才能回家。因?yàn)榈玫韧饣饘⒏G里的雜木引燃才放心。窯心未起火,白天的火就等于白燒。無(wú)論回去多晚,父親都不會(huì)空手回,他還要挑擔(dān)柴火回去。燒炭季節(jié)我們就無(wú)需上山砍柴了。
一般燒兩天兩晚就可以封窯。碰上雜木粗大,也可能延時(shí)。母親看煙的經(jīng)驗(yàn)還是管用的。父親當(dāng)然更清楚火候。他總是最先醒來(lái)的人。醒來(lái)就抽煙,用舌頭卷過(guò)來(lái)再卷過(guò)去。被褥上滿是煙灰烙的洞洞。父親擔(dān)心窯火。
燒窯、封窯的日子父親繼續(xù)揮舞鋒利的斧子,準(zhǔn)備下一窯的雜木。
三天后,摸摸窯門(mén)涼了就正式出窯。父親皺紋笑成了一堆。他先將一截過(guò)了水的臘肉插上筷子,虔誠(chéng)地祭過(guò)叫祝融的火神,然后撬開(kāi)窯門(mén),像接生一樣小心翼翼出炭。再三叮囑我們要小心輕放,不要抖掉了木炭上那層薄薄的白沫子。這是好炭的標(biāo)志。父親從窯里伸出頭時(shí),滿臉烏黑,眼睛卻閃爍著光彩。父親從不用蛇皮袋或麻布袋裝炭。他用自己織的竹篾箕,下邊裝碎炭,上邊裝粗炭,既不會(huì)弄碎炭,好炭差炭也不遮遮掩掩,一眼看得清清楚楚。狡猾的燒炭人會(huì)將煙腳用煙子熏黑。父親發(fā)現(xiàn)帶煙腳的炭,哪怕僅僅一小截,都會(huì)狠狠敲掉,挑回來(lái)自家燒,燒得滿屋子煙霧繚繞。弟弟這時(shí)背著手唱:黃煙煙莫煙我,煙死對(duì)面山上的黃子狗。而我想,父親燒炭,家里居然沒(méi)燒過(guò)一爐好炭火,好炭火都要賣(mài)給別人。
賣(mài)炭火,只在天寒地凍時(shí)走俏。父親巴望雪下得猛烈而漫長(zhǎng)。但母親很擔(dān)心父親,冰凍天里,將炭挑下山是件艱難的事情。母親用布條混合稻草做成的草鞋,既暖和又防滑。上山時(shí),父親用鋤頭刨出一個(gè)個(gè)坎,下山時(shí),石頭光滑,仿佛光溜溜的魔芋。母親讓我們每天放學(xué)去給父親背炭。去炭窯的山路早被父親清掃得平坦而寬闊,狹窄的地方還用木頭架個(gè)懸橋。
有一天,月亮升老高了,父親還沒(méi)回家。我們尋到半山腰,發(fā)現(xiàn)父親連人帶炭一起埋在雪堆里,冒出半邊身子。他已經(jīng)凍僵了,手腳動(dòng)不了,嘴里卻還嚎著山歌。
父親的第一擔(dān)木炭一定給外祖母送去。這個(gè)規(guī)矩從父親開(kāi)始燒炭就堅(jiān)持。外祖母最怕冷,一起風(fēng)就瑟瑟抖顫。
爹親娘親,不如一爐炭火親。父親給外祖母送的木炭,讓外祖母的心暖暖的。她把新炭放進(jìn)旺旺的火爐,火光輻射到她的身上,說(shuō),崽呀,就你對(duì)我好!外祖母說(shuō)罷離開(kāi)廂房,在廚房木梁上用鐵鉤子扒出一塊黑漆的臘肉,遞給了父親。
父親也不客氣,拿到窯山,把臘肉煮了,還在石頭灶里埋入幾個(gè)紅薯,中午就能用臘肉伴香甜的烤紅薯吃。
父親挑炭,肩上長(zhǎng)出一個(gè)個(gè)黑黑的坨。母親說(shuō)是肩坨。肩膀經(jīng)常費(fèi)力的人,都會(huì)長(zhǎng)出這種粗糙的東西。有時(shí),父親要我用力按摩那肩坨,好像他不知道疼痛。我掐著掐著,不一會(huì)兒,父親便耷拉下腦袋,響起隆隆的鼾聲。
父親燒炭,多是雜木炭。雜木炭的品質(zhì)好,自然也不愁銷(xiāo)路。父親只要將木炭擺上墟市,顧客便紛紛圍攏過(guò)來(lái),幾乎不討價(jià)還價(jià),付了錢(qián),挑上木炭就走。
老顧客還樂(lè)意到山上去挑。顧客上山,父親就只能讓我們兄弟提前下山。意思是有臘肉的那份噴香的柴火飯得讓給客人了。我們空著肚子,背著木炭極不情愿地高一腳矮一腳往回走。
父親燒窯,從初冬一直燒到過(guò)年。
過(guò)年的時(shí)候,因?yàn)楦赣H燒窯賺了錢(qián),我們除了有新衣裳穿,還會(huì)給我們每人嶄新的壓歲錢(qián)。母親也會(huì)給黑黑的父親縫制新棉襖,換個(gè)新的耷耳帽。
這時(shí)候父親豪爽地給自己放一兩天假,最多閑到初五六,便又燒窯了。初一吃過(guò)年飯,父親就提著一面銅鑼沿村子敲打:唱花鼓戲咯!唱花鼓戲咯!這時(shí),大院子里的戲臺(tái)又派上了用場(chǎng)。父親和他的伙伴們,描腮涂眉,套上花花綠綠的戲服,爬上戲臺(tái)咿咿呀呀地唱。父親喜串老生,模樣兒像了,腔兒也足,竟能引得一片喝彩。父親很得意自己的這個(gè)角色,他喜歡把整個(gè)山村的溫暖,在春節(jié)時(shí)推向另一個(gè)愉快的潮頭。
我后來(lái)才知道,沒(méi)有父親的村子有多寂寞。我們村里,不是缺了父親就唱不成花鼓戲了,而是唱戲時(shí),缺少一個(gè)慷慨舍木炭的燒窯人。這時(shí)的戲臺(tái)上下,寒風(fēng)逼人,父親忙從家里挑出一兩擔(dān)好木炭,放在戲臺(tái)旁任人燒烤。火盆里的木炭紅彤彤的,高高的火焰,舔得戲兒更有味道。看戲的人,袖著手,守著爐火不想動(dòng),聽(tīng)?wèi)蚶锏能浾Z(yǔ)高腔,任雪花簌簌地下。
作者簡(jiǎn)介:劉立勇,湖南省作協(xié)教師分會(huì)會(huì)員、婁底市作協(xié)會(huì)員。有作品在《湖南工人報(bào)》《今日女報(bào)》《莫愁》《湖南散文》《愛(ài)你》《中國(guó)教師報(bào)》《農(nóng)民日?qǐng)?bào)》等報(bào)刊發(fā)表。
責(zé)編:扶雄芳
一審:鐘鼎文
二審:熊敏
三審:羅曦
來(lái)源:冷水江市融媒體中心
燒窯
劉立勇
稻谷入倉(cāng),紅薯落窖,秋的頭一拱,天氣就涼了。
稻草垛立在空蕩蕩的田野中,安靜、閑適。父親坐門(mén)檻上掏出火鐮,點(diǎn)燃老旱煙,仰望蒼穹下莽莽的九龍山。九龍山像九條騰躍的龍,尾擺頭揚(yáng)。此刻,它也像父親翻滾的心事,澎湃不已。父親正思慮把小炭窯擴(kuò)建成一窯產(chǎn)一千斤的大窯。你想,燒一窯炭大概需要一個(gè)星期,倘若一窯有一千斤,整個(gè)冬季的收入就可觀了。
天剛蒙蒙亮,我們還在賴(lài)床,父親起了床,帶著汪汪叫了幾聲的黃狗,沒(méi)入了林子。林子里很快響起父親高亢的山歌。喜鵲和斑鳩撲棱棱竄出樹(shù)蔭。
在這座山里,山下和山腰都是高大茂盛的杉樹(shù)松樹(shù),就山頂一圈兒,全是矮實(shí)的雜木,譬如櫸木、黃楊、柞樹(shù)、楸木、野栗子樹(shù)……這些樹(shù)木在山頂生長(zhǎng)十年、二十年,還是那么大個(gè)兒,根本無(wú)法看出它們的真實(shí)年輪。只有透過(guò)細(xì)密的紋理、褐亮的樹(shù)皮,方能感知它們?cè)陲L(fēng)雪里不屈的磨礪。
山里,每天都是這樣,早晨,太陽(yáng)最先給山頂抹上一層金黃,蒼老的樹(shù)皮上反射著煦暖的光芒,格外耀眼。然后光暈漸漸浸潤(rùn)山腰、山腳。太陽(yáng)落到山澗時(shí),差不多正午了。要是冬天,雪帽兒也最先覆蓋住這些堅(jiān)硬的雜木。
父親差不多和太陽(yáng)同時(shí)爬到山巔。父親朝手心哈一口熱氣,再使勁搓搓,又嚎幾句滾板調(diào)。山底下的木屋飄起裊裊炊煙。那樣苦難的日子,我從沒(méi)見(jiàn)過(guò)父親有半點(diǎn)頹廢。父親是我心中的標(biāo)桿,也像山頂巖壁上最堅(jiān)硬的一棵雜木。
炭窯建在當(dāng)陽(yáng)的風(fēng)口最好。當(dāng)風(fēng),火燃得更旺。而且最好能遠(yuǎn)遠(yuǎn)望得見(jiàn)家。那是母親的意思。盡管母親看不到父親貓窯里裝窯、出窯,但她可以看到窯頂?shù)臒煛8G頂冒濃黑煙時(shí),就知道父親燒窯了;煙豎得筆直時(shí),就是窯火燃旺了;像水墨畫(huà)一樣淡了、散了,就是該封窯了;天空干凈得只看到藍(lán)柔柔的底時(shí),就可以出窯了。
母親沒(méi)上過(guò)山,但母親喜歡遠(yuǎn)遠(yuǎn)地看山上的煙。
父親的炭窯比別人筑得精致。整個(gè)外形像個(gè)隆起的蒙古包。最外層涂抹的黃泥,父親用細(xì)篩過(guò)濾了一遍又一遍,光滑細(xì)膩。窯口方正的大麻石,還是父親從澗底挑上來(lái)的,砌得工工整整,出窯裝窯極為方便。四根粗壯的松木支撐杉木皮棚頂,就煙囪孤零零地插向天空。一千斤的炭窯顯得好敞闊,父親在炭窯里美美地躺了一袋煙的功夫。
砌好窯就可以正式燒炭了。先砍伐雜木。父親戴著耷耳帽,像只啄木鳥(niǎo),邦邦邦,木屑飛濺。雜木紋理細(xì)密堅(jiān)硬,碰到碗口粗的還需要斧子。嘩啦砍倒,削了細(xì)枝和樹(shù)葉,光木頭滾到窯旁的空坪,堆成小山。再下來(lái)用斧頭斫成短木段。父親的手法真好,好像每一截都精準(zhǔn)測(cè)量了一般,都剛好斫成一米長(zhǎng),在窯旁碼得整整齊齊。斫木頭時(shí)父親會(huì)將破棉襖甩得遠(yuǎn)遠(yuǎn)的,也不戴耷耳帽,哪怕下雪冰凍天,父親的頭頂都會(huì)直冒熱氣。父親一天要磨兩次砍刀和斧子。手掌虎口都震裂了,用膠布纏了一層又一層。雜木林偶爾也生出數(shù)根杉木、松木。但父親是不用杉木、松木燒炭的。那屬于泡木,泡木燒炭不亮火。雜木燒出的炭才易燃、耐燒,而且一燃熱氣就蹭蹭地上身。像櫸木炭、楸木炭、寡木子炭,還會(huì)發(fā)出歡快的啪啪聲,火星濺到褲腰上。
看著夠一窯的雜木就裝窯了。裝窯時(shí)還得有個(gè)好幫手。所以父親選擇我們放學(xué)時(shí)裝窯。父親弓著身子在窯里,我們負(fù)責(zé)將木頭搬運(yùn)到窯口。裝窯也有技巧,一般將小一些的雜木放外圍,粗壯的放中間,要擠得嚴(yán)嚴(yán)實(shí)實(shí),木炭才不會(huì)燒透。木頭也不能插入泥土,插入泥土就有煙腳。
封好窯,父親才可以歇口氣。然后在窯口燃起大火。山下的母親一抬頭就知道父親燒窯了。父親得很晚才能回家。因?yàn)榈玫韧饣饘⒏G里的雜木引燃才放心。窯心未起火,白天的火就等于白燒。無(wú)論回去多晚,父親都不會(huì)空手回,他還要挑擔(dān)柴火回去。燒炭季節(jié)我們就無(wú)需上山砍柴了。
一般燒兩天兩晚就可以封窯。碰上雜木粗大,也可能延時(shí)。母親看煙的經(jīng)驗(yàn)還是管用的。父親當(dāng)然更清楚火候。他總是最先醒來(lái)的人。醒來(lái)就抽煙,用舌頭卷過(guò)來(lái)再卷過(guò)去。被褥上滿是煙灰烙的洞洞。父親擔(dān)心窯火。
燒窯、封窯的日子父親繼續(xù)揮舞鋒利的斧子,準(zhǔn)備下一窯的雜木。
三天后,摸摸窯門(mén)涼了就正式出窯。父親皺紋笑成了一堆。他先將一截過(guò)了水的臘肉插上筷子,虔誠(chéng)地祭過(guò)叫祝融的火神,然后撬開(kāi)窯門(mén),像接生一樣小心翼翼出炭。再三叮囑我們要小心輕放,不要抖掉了木炭上那層薄薄的白沫子。這是好炭的標(biāo)志。父親從窯里伸出頭時(shí),滿臉烏黑,眼睛卻閃爍著光彩。父親從不用蛇皮袋或麻布袋裝炭。他用自己織的竹篾箕,下邊裝碎炭,上邊裝粗炭,既不會(huì)弄碎炭,好炭差炭也不遮遮掩掩,一眼看得清清楚楚。狡猾的燒炭人會(huì)將煙腳用煙子熏黑。父親發(fā)現(xiàn)帶煙腳的炭,哪怕僅僅一小截,都會(huì)狠狠敲掉,挑回來(lái)自家燒,燒得滿屋子煙霧繚繞。弟弟這時(shí)背著手唱:黃煙煙莫煙我,煙死對(duì)面山上的黃子狗。而我想,父親燒炭,家里居然沒(méi)燒過(guò)一爐好炭火,好炭火都要賣(mài)給別人。
賣(mài)炭火,只在天寒地凍時(shí)走俏。父親巴望雪下得猛烈而漫長(zhǎng)。但母親很擔(dān)心父親,冰凍天里,將炭挑下山是件艱難的事情。母親用布條混合稻草做成的草鞋,既暖和又防滑。上山時(shí),父親用鋤頭刨出一個(gè)個(gè)坎,下山時(shí),石頭光滑,仿佛光溜溜的魔芋。母親讓我們每天放學(xué)去給父親背炭。去炭窯的山路早被父親清掃得平坦而寬闊,狹窄的地方還用木頭架個(gè)懸橋。
有一天,月亮升老高了,父親還沒(méi)回家。我們尋到半山腰,發(fā)現(xiàn)父親連人帶炭一起埋在雪堆里,冒出半邊身子。他已經(jīng)凍僵了,手腳動(dòng)不了,嘴里卻還嚎著山歌。
父親的第一擔(dān)木炭一定給外祖母送去。這個(gè)規(guī)矩從父親開(kāi)始燒炭就堅(jiān)持。外祖母最怕冷,一起風(fēng)就瑟瑟抖顫。
爹親娘親,不如一爐炭火親。父親給外祖母送的木炭,讓外祖母的心暖暖的。她把新炭放進(jìn)旺旺的火爐,火光輻射到她的身上,說(shuō),崽呀,就你對(duì)我好!外祖母說(shuō)罷離開(kāi)廂房,在廚房木梁上用鐵鉤子扒出一塊黑漆的臘肉,遞給了父親。
父親也不客氣,拿到窯山,把臘肉煮了,還在石頭灶里埋入幾個(gè)紅薯,中午就能用臘肉伴香甜的烤紅薯吃。
父親挑炭,肩上長(zhǎng)出一個(gè)個(gè)黑黑的坨。母親說(shuō)是肩坨。肩膀經(jīng)常費(fèi)力的人,都會(huì)長(zhǎng)出這種粗糙的東西。有時(shí),父親要我用力按摩那肩坨,好像他不知道疼痛。我掐著掐著,不一會(huì)兒,父親便耷拉下腦袋,響起隆隆的鼾聲。
父親燒炭,多是雜木炭。雜木炭的品質(zhì)好,自然也不愁銷(xiāo)路。父親只要將木炭擺上墟市,顧客便紛紛圍攏過(guò)來(lái),幾乎不討價(jià)還價(jià),付了錢(qián),挑上木炭就走。
老顧客還樂(lè)意到山上去挑。顧客上山,父親就只能讓我們兄弟提前下山。意思是有臘肉的那份噴香的柴火飯得讓給客人了。我們空著肚子,背著木炭極不情愿地高一腳矮一腳往回走。
父親燒窯,從初冬一直燒到過(guò)年。
過(guò)年的時(shí)候,因?yàn)楦赣H燒窯賺了錢(qián),我們除了有新衣裳穿,還會(huì)給我們每人嶄新的壓歲錢(qián)。母親也會(huì)給黑黑的父親縫制新棉襖,換個(gè)新的耷耳帽。
這時(shí)候父親豪爽地給自己放一兩天假,最多閑到初五六,便又燒窯了。初一吃過(guò)年飯,父親就提著一面銅鑼沿村子敲打:唱花鼓戲咯!唱花鼓戲咯!這時(shí),大院子里的戲臺(tái)又派上了用場(chǎng)。父親和他的伙伴們,描腮涂眉,套上花花綠綠的戲服,爬上戲臺(tái)咿咿呀呀地唱。父親喜串老生,模樣兒像了,腔兒也足,竟能引得一片喝彩。父親很得意自己的這個(gè)角色,他喜歡把整個(gè)山村的溫暖,在春節(jié)時(shí)推向另一個(gè)愉快的潮頭。
我后來(lái)才知道,沒(méi)有父親的村子有多寂寞。我們村里,不是缺了父親就唱不成花鼓戲了,而是唱戲時(shí),缺少一個(gè)慷慨舍木炭的燒窯人。這時(shí)的戲臺(tái)上下,寒風(fēng)逼人,父親忙從家里挑出一兩擔(dān)好木炭,放在戲臺(tái)旁任人燒烤。火盆里的木炭紅彤彤的,高高的火焰,舔得戲兒更有味道。看戲的人,袖著手,守著爐火不想動(dòng),聽(tīng)?wèi)蚶锏能浾Z(yǔ)高腔,任雪花簌簌地下。
作者簡(jiǎn)介:劉立勇,湖南省作協(xié)教師分會(huì)會(huì)員、婁底市作協(xié)會(huì)員。有作品在《湖南工人報(bào)》《今日女報(bào)》《莫愁》《湖南散文》《愛(ài)你》《中國(guó)教師報(bào)》《農(nóng)民日?qǐng)?bào)》等報(bào)刊發(fā)表。
責(zé)編:扶雄芳
一審:鐘鼎文
二審:熊敏
三審:羅曦
來(lái)源:冷水江市融媒體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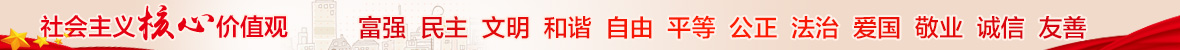
!/ignore-error/1&pid=45434035)
!/ignore-error/1&pid=14055395)
!/ignore-error/1&pid=50436665)
!/ignore-error/1&pid=469166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