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 大熊山印象——龍項滔
大熊山印象
龍項滔
因為蒼天在上
我愿意埋首人間
——張二棍
1
我這半生,與山為伴。山外有山,山像一道道藩籬圈定了我的人生。與山相處,不得不虛心接受山的逼視,在山面前,人必須低調謙遜。人輕山重,是命運的壓迫,也是饋贈。人生最理想的狀態莫過于與山兼容,爬上山頂,親手摘下白云;或站立山巔,吞納萬頃波濤,何其幸也?只是我身邊的山,大多數荊棘密布,道路難行,進山已屬不易,登頂自然成了奢望。
人都希望自己的一生像鳥那樣活得很遼闊,像高山那樣活得巍峨,所以總想著浮于云端俯視天下,做一個巨人,似乎是生活的低海拔,拔高我們了對高度的敬仰。
那座能滿足我的攀登欲、能減輕生活之重的山在哪里呢?
大熊山地處湘中,距離我家僅八十公里,我們同市不同縣,算是鄰居。距離雖然很近,但直到2019年之前只聞其名未見其容。未身臨其境之前,大熊山在我的想象中,或茂林修竹、清流激湍;或層巒疊翠、古木參天;或云霧繚繞、遍地花香。也曾經想過邀三五好友,或徜徉于林下,或逐水于清溪,或尋香于花海,或長嘯于云端。但去過之后,發現它并沒有想象中那么古典和浪漫。表面上看,與我身邊的山并沒有太多區別。且每次去大熊山都是獨來獨往,行色匆匆。未成行之前向往,成行之后失落。于是感慨在一段蜿蜒曲折的路途中,耗費了錢、汽油,耗費時間和精力,收獲的卻是一身的疲憊。
唉,人生不就是如此嗎?
幸好,它離我很近,在想去就去的范圍之內,我也是在與它多次的接觸中漸漸喜歡上了它。我喜歡在持續不斷上升中獲得與風迎面相撞的快感。我喜歡春姬之水,常常溯溪而上直達涌泉。我也喜歡天香的清溫,喜歡躺在衣袂飄飄的彩繪中,做一個朱紅色的夢。我喜歡深入林中,踩響落葉的琴鍵。每次去大熊山,我都要去看一看老樹的鋼筋鐵骨,都要在綿延的蒼涼中放生憂慮。
大熊山,它是一處寬闊且內涵豐富的精神牧場。
2
嚴格來講,我去大熊山,不屬于旅游。有時候在家閑來無事,想出去走走,首選就是它。從這一點來說,更像是閑逛。既然是逛,一切都很隨意,自然會發生許多趣事。
2020年7月9日。同樣是臨時起意,和一個朋友相約去大熊山。那天天晴氣溫較高,加之山陡路彎,朋友暈車嚴重,出發之前的美好心情在半途之上就打了折扣。行至月牙灣度假村處,朋友說眩暈得厲害,不想再往上走了。我便將車停在空坪,發現此處有一游步道,隱于林中,便提議沿游步道走走,一來緩解一下身體的不適,二來往山中走走,也算是到此一游。步道一米多寬,隨山勢徐徐往下。曲徑通幽處、路陡林深,人隱于林中,陽光被高大的喬木遮擋,徐徐清風穿過林木的空隙,頓感涼風撲面,暑熱便消了大半。
沿步道走了約一二百米,碰到一處觀景臺。此處是大熊山之陰,下方便是大名鼎鼎的春姬峽。站在此處,潺潺流水之聲不絕于耳。順狹谷出口往遠處觀望,只見滿目青山之上,流云似雪。在此極目遠眺,只見青山嵯峨綿直,更兼鳥語蟬鳴,頓覺心神清爽了許多。
原路返回時,我發現一處灌木叢中有一種我特別熟悉的東西——樅樹菇(土語名樅樹菌)。這是山中一種可食用的野生蘑菇,六月的樅樹菇表面呈淺黃色,中間有一圈不太明顯的白紋,里面則是淺紅色,呈散熱片狀。
既然路邊有,山里肯定有。我說。
那就進山找找。朋友也來了興致。
于是,我們便鉆到灌木與馬尾松混雜的密林中尋找,果不其然,驚喜一個接著一個。
繼續往上,爬至山頂一緩坪上,見厚實如毯的腐葉之中,樅樹菇到處可見,僅用不到一個小時的時間,便采拾了幾大袋。我這一輩子,從小便識菇采菇,卻從未見過菇如此普遍。驚喜之余,心中非常疑惑:此處雖是半山腰,但并非人煙稀罕處,這么多野生蘑菇為何無人發現,無人采拾?難道當地人不認識?或者是我偷竊了別人的私種?
這一次意外的收獲誤導了我好多年,每年一到六七月份,便想起大熊山的樅樹菇,總要抽出時間到那地方看看。但奇怪的是,同一季節同一地點,我再沒有找到哪怕一個菇子。每次攜帶著興致去,空空落落回。樅樹菇如同不足為外人道的世外桃源,再沒有第二次重現人間。
3
每次去大熊山,都是從蚩尤屋場往上,至熊山古寺至大熊峰,這是一條常規的線路。熊山古寺恰好位于這條常規線路的中段,近似于一個驛站。
在我的印象中,每次去熊山古寺,天氣都不太好。出發時,明明天氣晴好,可踏入熊山古寺中,便可見天邊飄來一大片陰云籠罩在古寺之上,許久不再挪開。有時候去時本就是一個陰天,在古寺停留時,天空竟下起雨來。古寺永遠是那樣陰郁,從來沒有對我笑過,像一個古板的老人。雖為古寺,我卻沒有一次見到它人聲鼎沸的樣子,名山古剎門檻被踏破的現場,在熊山古寺里我沒有碰到過。人少則靜,在這里,哪怕是一只在大理石臺階上攀爬的黑螞蟻,我也能聽到它的喘息聲。在這里走走,沒有人向我兜售開過光的佛珠,沒有向我推銷糖果可樂。它允許我囊中羞澀,允許我無所事事。
其實它的年齡也不小了,始建于兩晉時期,約一千多歲了。年老封神,它完全有理由打開山門,接受更多人的頂禮膜拜。
因為是一粒塵埃,所以才向往滿天星光。像我這種俗人:愛得猶猶豫豫,恨得膚膚淺淺,半生歷程幾無亮點。所以每到一處大殿,我都要上香跪拜,在各路大神面前低頭。凡間并無神靈,但我認為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寄存美好的佛殿。在神面前,我滿身塵污,我無限慚愧,但在這里,我能找到被我丟棄的自己,他那么干凈,他比我高尚許多。有那么一瞬間,我真的不想走了,多么想在此結一草廬,寄宿林下了此余生。“便此地、結吾廬,待學淵明,更手種、門前五柳”。但我很快否定了這種可能,我太怯懦,無法放棄人世間的那個我,無法把身子擦得干干凈凈。修行是為了建一座心靈的宅院,我已無心也無力將它建成了。
2023年3月,我同妻兒再一次游歷了大熊山。依然是一個陰天,進入熊山古寺后,下起了毛毛細雨。這一次,我們在寺里停留的時間比較長。妻子是一個信神信佛的人,總認為世間一切神靈可控,所以每進一次大殿,便要求兒子和她一起跪拜,虔誠之心溢于言表。那年,兒子高三,再過不到三個月,便將迎來高考。他就讀的學校是一所普通高中,盡管他非常努力,在高中時期成績一直名列前茅,一直拿獎學金,但和重點中學的優秀學生比,成績還是有明顯的差距。我本是個唯物主義者,但在兒子的前程上,多少表現得有點唯心,所以不僅沒有反對她們有點夸張的虔誠,自己也躬身下拜,甚至在千年銀杏樹前,也和其他人一樣,將一根寫滿祝愿的紅絲帶系在了大樹的樹枝上,祈愿家人身體健康,兒子學業有成。都說時間能渡劫一切,銀杏能歷盡千年的風霜仍然枝繁葉茂,生存便是一個奇跡,在人間,奇跡的存在暗示著無限可能。
人一旦心存信仰,便能勇敢無畏。人一旦把某物視為信仰,便相信信仰有無窮的力量。這棵古老的銀杏樹上,掛滿了祝福和祝愿。我知道這滿樹的期許,未必都能美好如愿,人間事最終還是事在人為,但紅絲帶飄著,飄著的是向往,而向往,即指引方向的導航。
4
關于大熊山,我曾經寫過一首短詩:
越往上走
山越老
越往上走
越能感受到頭頂的荒涼
但如果不爬
又怎能懂得灌木如何朽折
又怎會心疼秋風吹落了
哪棵樹的羽毛
有一次和一友人登頂大熊峰,兩個人在峰頂的大霧中四目相對。朋友說:幾年時間,你我都蒼老了許多。有感于人到中年,青春已逝,于是便有了這首詩。
大熊峰身高1622米,貴為湘中第一高峰,但其峰頂上除了留守在山頂的一片灌木叢和被雨雪風霜摧殘了上百年、存量并不多的高齡老樹,既無奇峰也無怪石,令人驚艷的景色并不多。登頂大熊山,大多數人在觀景平臺上俯視山下,拍個照發個朋友圈,然后丟掉手中的礦泉水瓶,扔下一句:沒多大意思。
其實只要有心,仔細觀察,大熊山山頂是有景可看的,比如那一大片竹林。一般的箬竹莖并不粗,約小指大小,但能長一二米高。大熊山山頂的箬竹明顯矮小瘦弱。一般一片箬竹葉足有三四厘米寬,二三十厘米長,一片箬竹葉可包一個小粽子。但大熊山山頂箬竹葉片細小了將近一半。因為常處在多風多雨多雪的山頂,這里的箸竹為了生存,主動改變,它們將身姿放低,葉片變細,且密密匝匝擠在一起,抱團取暖。
我喜歡古林棧道那一片古木,到了山頂,無論天氣如何,我都要去看看它們。那些身披青苔的四照花、扇葉槭、云錦杜鵑,都年逾百歲。表皮已呈鋼鐵之色,且附滿青苔。它們的枝干,沒有一棵是筆直的,身上那些被折斷的傷痕仍在,生命始終在折斷處重生,生活始終在不斷曲折中前行。虬枝亂舞,時間將它們塑造成一個個狂草藝術家。每次去,不喜歡拍照的我,總要與它們合個影。
幾年前,我曾在路邊的那棵孤獨的扇葉樹下拍照留念。那個時候,我頭頂還算茂盛,面目尚存英氣。幾年之后,我攜帶滿身疲憊再去看它時,它也已風燭殘年了。伸展如翅膀的粗枝已經不見了,整樹幾成光桿,往日繁華不再,心中不禁傷感。
和熊山古寺那棵千年銀杏相比,大熊峰頂的老樹普遍年輕很多,受到的關注也少很多。但它們同樣值得我們敬佩。我很慶幸拍下了那些與古樹的合影,它不僅僅是我生命的記錄,也是這些植物存世的記錄。但拍照技術再好,也無法拍下整樹的形韻。我一直很遺憾沒有學會繪畫,所以無法用線條將樹描繪出來,其實每一棵古樹都是一幅幅精美的畫作。
一直也想用文字好好記一記大熊峰頂這些了不起的植物,總覺得詞不達意,怎么寫都不準確。
大熊山橫跨新化、安化兩縣,區域面積大,可探險的地點和項目較多,但我每次去都是循規蹈矩,沿著熟悉的路線走一遍。我已經深深愛上了那條上山的路徑,深深愛上它的安靜、空闊和蒼涼。多次沉浸于山中,做一個孤獨的路人,我發現天地之間的我已不再是我。
我發覺人生的高處,永遠是從生活的最低處起步。
作者簡介:龍項滔,婁底市作協理事,有作品發表于《羊城晚報文藝副刊》《湖南文學》《當代詩歌》等刊物,有散文被《美文》等雜志轉載。
責編:楊雅婷
一審:鐘鼎文
二審:熊敏
三審:羅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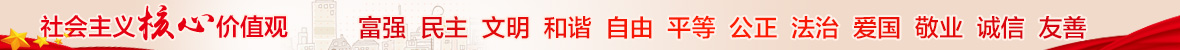
!/ignore-error/1&pid=45434035)
!/ignore-error/1&pid=14055395)
!/ignore-error/1&pid=50436665)
!/ignore-error/1&pid=469166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