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 屋上春鳩鳴——周雪輝
屋上春鳩鳴
周雪輝
我居住的小區,有個小園子,約莫半個足球場那么大,草木繁盛,眾鳥啁啾。那些鳥兒,我大多叫不出名字,也難以近距離觀察到,它們常常成群結隊藏匿在如蓋的樹冠里。
春日午后,我在書房正讀到王維的那句“屋上春鳩鳴,村邊杏花白”,忽聞窗外有咕咕咕的鳥叫聲,那么近、那么真,似在耳畔。我輕輕地拉開紗窗,一只大鳥撲騰著翅膀,從窗前“呼”地飛去。我四處探望,發現窗外一米處的空調外機架上,在空調外機和墻壁之間,有一個鳥巢。這是一個簡單的巢,大小和形狀類似于一只平底的菜碟,由細樹枝、樹杈交織堆疊而成的鳥巢。兩只如明珠般潔白的蛋,靜靜地臥在里面,發著亮光。那被驚飛的大鳥,在不遠處來回踱著步,晃著腦袋,眼睛不知是看著我,還是看著鳥巢。我知道這簡單的鳥巢,就是鳥的家。我關上了窗戶,拉好窗簾,退到客廳,我的心情瞬間沉重起來,感覺自己貿然闖進了鄰居家,我在心里期盼著鳥兒能早點歸巢,回到自己的家。我悄悄地退卻,為了讓鳥兒能安心地回巢。
傍晚時分,晚霞如虹。我輕輕拉開紗窗,爬上書桌,緩緩地探出頭去。一只褐色羽毛的斑鳩正臥在巢中,它身材頎長,紡錘形的身體線條流暢,頭部為鴿灰色,通體多為褐色,前頸和腹部顯出粉紅色來,斑鳩的后頸很漂亮,仿佛搭著一件綴著白珍珠的黑色披肩。它的學名應當是珠頸斑鳩,也就是我們常說的“野鴿子”。
它偏著頭,眼神中略有些警覺,雙翅輕輕地往外頂起,仿佛隨時準備飛離。它發現我了,我隨即收回身體,輕輕地關上紗窗,小心翼翼地下了書桌。在電腦上打上一行字來,“今天,我家搬來了新鄰居,與鳥為鄰,是一個值得高興的日子。”
鳥在窗外,我在屋內,我們各自享受著歲月靜好。既相互陪伴,又不彼此叨擾,日子如水,靜謐安詳。鳥兒不時地發出幾聲“咕咕”的叫聲。我也不時地探出頭,看看彼此間是否安好。有時,我還看到另外的一只鳥也會守在巢邊,只是還沒等我靠近,它就遠遠地飛走了。我在想,這大概是這鳥巢的男主人。也許是對我還不太熟悉,充滿著警戒。
原來是這只大鳥在孵小鳥了,一連20多天,我都看著它臥在巢里,偶爾還有那只不認識我的鳥,有時,兩只鳥都蹲在鳥巢中。有一天,我聽到了幼鳥的啁啾聲,我看到兩只雛鳥趴在巢中。灰不溜秋,一點都不好看,十多天后,雛鳥體型大了,仍是炸著一身灰色毛羽。兩只大鳥輪流地喂養雛鳥。它們長得太像了,分工合作,輪流值班,我安能分辨雌雄。
一年又一年,它們戀愛、結婚、生育,一夫一妻,彼此忠誠,共同培養孩子,待到雛鳥離巢,再孕育下一批孩子。鳥的一生也如人一般,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忙忙碌碌,彈指間便是一輩子。
我的女兒正在深圳讀大學,每年的寒暑假回家,正如鳥兒歸巢,而我靜靜地守著老巢,候著孩子歸來,一年又一年。
我守著我的家,看著我的女兒,她青春曼妙、神采飛揚、意氣風發,她如同羽翼漸豐的雛鳥般,躍躍欲試,隨時準備飛離。我也知道,我終究是不能一生陪伴孩子的,我終究只能目送,目送她飛向更高更遠的天空。
今年的疫情無常,母親的身體有恙。我陪母親去省城體檢、治療。為了防疫,醫院,小區、賓館,甚至去超市,隨時要掃健康碼、行程碼。醫院猶如迷宮,此門進,彼門出。對于我來說,倒只是麻煩,但還是能轉得明白,也轉得出門來,可對于我的母親,離開我,她幾乎寸步難行。
這天早晨,我陪著母親到了湘雅附二外科樓一樓。幾個保安守著狹窄的門,憑導診單和健康碼進入。我是希望陪著母親一起進去的,卻被保安擋在了門外。我隔著玻璃,看到母親卻如孩童般,怯怯地走過去,在右側排著隊。那里有好幾個窗口,她卻站在了人最多的隊伍后面。我好想喊她站到病人少的那兒去,可是她聽不見我的呼喊,也看不到我。沒多久,我竟然看不到我的母親了,哪去了?我向里張望著,透過厚重的墨綠色的天鵝絨窗簾的縫隙。
此時的情景竟讓我回想起我的孩子,當她第一次上幼兒園時,當她第一次住校時,把她送進校園的我,也是這般,懷著不舍,懷著擔憂,往里張望,張望。母親老了,老成了一個孩子,她弱小、膽怯、無助,她需要我的指引、保護與呵護,如同我小的時候,她護著我一般。
母親進手術室前,我摟著母親,不停地寬慰著她。醫生勸導我,不要在手術室外逗留。母親進手術室后,不到一個小時,我接到了醫生的電話,通知我去談話室。是王醫生,他穿著手術服,在一個小小的窗口里,他面前有一個手術托盤,上面放著一個腫瘤狀物。“手術很順利。”他用手撥弄著眼前這一大坨東西,應該有二三斤,白色帶著血管網,完整光滑,似乎有一層膜,軟得像脂肪。“以我們的經驗來看,是良性的,現在需要做一個快速的病理檢測。”我驚訝地看著這么大一堆東西,這也太大了,幸虧是做了手術,多大的負擔啊。“很好,完整地剝離了。沒有傷到其他臟器。”我口里不停地說著感謝,手術成功了,良性,這真是不幸中的大幸運,我自言自語著。
我在五樓,等著母親醒過來。我看著不斷有病人從復蘇室被推了出來,有老有少,有男有女,甚至還有幾歲的幼童,就是不見我的母親。我身邊一個身形高大的中年女人,扶墻面壁,失聲痛哭,卻又在努力地壓抑著哭聲。這加深了我的焦慮,一個小時過去了,兩個小時過去了,三個小時過去了,我的母親怎么還沒有蘇醒過來。
大廳沒有椅子,很多的家屬席地而坐。我在手術室外足足站了四個多小時,沒喝水,沒上洗手間,我一刻也不敢離開,我怕我的母親醒來后看不到我,我怕她會害怕。下午一點零三分,我聽到了廣播,通知我去復蘇室。母親被推出來了,她看上去十分虛弱,面色發灰,眉頭緊蹙,嘴里輕喃,“好疼啊……”
我緊跟著醫生,上了20樓。我的父親托著母親的頭肩部,鄰床病友的家屬托著她的腰部,我托著腳,把母親移到床上。母親一直昏睡,醫生說麻醉蘇醒后的兩個小時不能讓她睡著,我一直在床邊輕輕地喚著母親,不時地用手撫摸母親的臉,讓母親保持清醒。我守護著術后的母親,如同守護著一個新生的嬰兒。
所謂父女母子一場,只不過意味著,你和他的緣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斷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漸行漸遠。你站立在小路的這一端,看著他逐漸消失在小路轉彎的地方,而且,他用他的背影默默告訴你:不必追。
而對于作為父母的我們,從第一次目送著孩子去幼兒園開始,我們已經在練習,練習著適應分離,孩子終將離父母遠行。父母目光就像一根長長的風箏線,這頭在自己的手中,那頭系在孩子身上,看著孩子越走越遠,越飛越高,我們何曾不心慌,何曾不忐忑。父母的目光始終追隨著孩子的身影。父母越來越老,越來越慢,終有一天,他們停下了,再也追不上了。
這時,我看到兩只稚鳥奮力地一躍,撲騰著翅膀,歪歪斜斜地飛離了鳥巢。一只大鳥正落在巢的邊沿,而另外的一只大鳥落在空調的外掛機上,它們的眼睛時而望著鳥巢,時而彼此對視著,時而望向那不斷試飛著的雛鳥。它們守護著彼此,守護著雛鳥,守護著它們共同的家。
我輕輕拉上紗窗,沒有去驚擾它們。鳥在窗外,我在屋內,我坐在書桌前,這里是我的家。“倦鳥暮歸林,浮云晴歸山。”倦鳥歸巢時,慈母倚門望子歸。
作者簡介:周雪輝,婁底市作協理事,中國金融作協會員,有作品見刊于《人民日報.海外版》《金融文壇》《寧鄉文藝》《金融博覽》《中國金融文學》《思維與智慧》《博愛》《今晚報》《長沙晚報》等報刊,獲湖南省金融作協主題征文二等獎。
責編:楊雅婷
一審:鐘鼎文
二審:熊敏
三審:羅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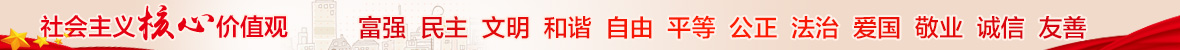
!/ignore-error/1&pid=45434035)
!/ignore-error/1&pid=14055395)
!/ignore-error/1&pid=50436665)
!/ignore-error/1&pid=469166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