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筠:富厚堂的女主人(散文)——胡曉霞
郭筠:富厚堂的女主人
胡曉霞
避亂始末
咸豐癸丑(1853)年三月的一天,一個(gè)七歲的小姑娘正在家塾讀《三字經(jīng)》。突然烏云密布,天色暗沉,視線模糊。父親皺著眉頭說:“這不是好兆頭,災(zāi)難就要來了。”果然,幾天后金陵(南京)失守,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guó)農(nóng)民起義風(fēng)起云涌。在父親的安排下,小姑娘的母親、庶母、兄弟姐妹輕裝逃亡至山西,打算在太原伯父署暫避。大難當(dāng)頭,天下都不太平,而伯母一家回了湖北老家。
此時(shí),小姑娘避難路上看到的景象是怎樣的呢?天將黑,水賊人多,各執(zhí)器械迎敵,終夜人聲震耳,大家恐懼,擔(dān)心在須臾之間便喪了命。天剛亮,船開時(shí),遠(yuǎn)遠(yuǎn)看到一幅觸目驚心的畫面,晚上殺戮的賊人已經(jīng)身首異處,一群野狗在啃噬他們的殘尸。
明明前一刻還是風(fēng)平浪靜,讀書學(xué)習(xí),頃刻間便是驟風(fēng)暴雨。寧做太平犬,不為亂世人。歷史的塵埃落在當(dāng)世的每個(gè)人身上都是一枚炸彈,成王敗寇,塵埃落定,而人性的奮發(fā)和進(jìn)取卻是永不泯滅的。
太平天國(guó)運(yùn)動(dòng)時(shí)期,普天皆無安土。父親補(bǔ)淮揚(yáng)道缺,一行人打算繞道趕赴父親處。黎明賊已入境,山路崎嶇,心里惴惴不安。而小姑娘此時(shí)卻見,深林處,大樹參天,金陽鋪地,耳邊泉水靜淌,百鳥和鳴,心里不禁神清氣爽。從清晨至中午都沒吃東西,饑腸轆轆,四肢像割斷了一般疼痛,二姐和庶母黃孺人臥在滑白的石上痛哭,愿就地而死。共計(jì)走了二十里,還剩五里。母親擔(dān)心他們露宿,非常著急,再三催促,才重新前行。憔悴不堪的樣子,破碎的衣服,官宦家眷,看起來卻同乞丐一般。
這便是清朝才女郭筠晚年的回憶文章《避亂始末記》里的故事。郭筠當(dāng)時(shí)不足十歲,此時(shí)正逢兵燹,經(jīng)歷了逃亡之凄苦。她的父親郭佩霖雖是與曾國(guó)藩同科進(jìn)士,但在郭筠十三歲父親就殉難于定遠(yuǎn),其時(shí)正在江蘇淮揚(yáng)道的任上。
我始終覺得要熟知一個(gè)人,特別是一個(gè)古人最好的方式是熟讀她的文字。郭筠在《避亂始末記》里按時(shí)間順序不僅寫到了亂世中的自己,還寫到了亂世中的普通老百姓,被蹂躪的中國(guó)。我能讀到的關(guān)于郭筠的文字并不多,所以更加仔細(xì),更覺珍惜。這篇文章還詳盡細(xì)膩真實(shí)地寫到了庚戌(1911)年的長(zhǎng)沙搶米風(fēng)波,當(dāng)時(shí)郭筠和家人就住在長(zhǎng)沙,親歷這事的始末。心中若沒有正義和對(duì)窮苦民眾的深切同情,若不夠勇敢,都是寫不出這樣飽含深情的文字的。在今天這樣物質(zhì)富足的時(shí)代,不妨再讀讀這些由于天災(zāi)人禍釀成的故事,也許會(huì)更懂得珍惜糧食,也許會(huì)更懂得感恩和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宣統(tǒng)己酉(1909)年,常德、沅江因去年水災(zāi)頗重,拔省中儲(chǔ)谷接濟(jì)。倉為之空,秋收驟難補(bǔ)足,加冬防不儲(chǔ),米糧逐日出境,官紳均不及慮,來春有缺乏之虞,余笑語家人曰:‘咨議局日日開會(huì),演說雖多,便無禁止谷米下河之說,此大錯(cuò)也,來年春間必荒無疑’于是,發(fā)谷三百石存于碓坊為來年食用之需,并囑迪軒,鄉(xiāng)谷留備來年,減糶,以濟(jì)貧者。”
宜統(tǒng)己酉年,三百石相當(dāng)于今天的三萬斤。郭筠此時(shí)已是六十二歲,經(jīng)歷了許多事后,對(duì)事情有了準(zhǔn)確地判斷,有了先見之明。于是備糧減糶,以濟(jì)貧者。
暴動(dòng)和亂子果然出現(xiàn)了。庚戌年(1910年)三月,城中米糧空虛,難以為繼。“南門處有一窮民賣河水度日,其婦積錢八十文,向碓坊買米,坊人刁難小錢,其婦負(fù)氣歸去,至第二天攜銅元八十枚,仍欲買米,坊人告以今日價(jià)增,不能賤售。此婦無錢,計(jì)無所出。而子女饑寒索食哭叫,其母以土巴巴煨熱置子女前。而自憤極,輕生,投于塘中。其夫回,知妻因貧而殞,義不獨(dú)生,于是攜子女三人赴水,一刻四命。于是街坊人大動(dòng)公憤……”大段大段細(xì)膩具體形象的文字背后可以看見那雙因不平而顫抖的手,那顆因同情而悲憤的心。
《避亂始末記》所記六十余年,最后郭筠說:“惟立德立言為道德之基礎(chǔ)。勉而行之,以教來葉,顯所屬望焉。”反復(fù)品讀,心亦久不能靜。外憂內(nèi)患的清政府,艱難度日的普通老百姓,昏官、奸商、暴徒、街痞、盜賊,命如草芥,民不聊生。文中所述之事距今一百多年,并不太遙遠(yuǎn),地點(diǎn)離我們的家鄉(xiāng)也不遠(yuǎn),讀來特別有感觸,難以想象這些事情曾發(fā)生在這片我們熟悉又陌生的天空下。
郭筠的文字真誠而生動(dòng),故事娓娓道來,吸人眼球,揪人心。一代才女的聰慧、勇敢、剛強(qiáng)、仁慈、正義都躍然紙上,顛沛流離,雖苦雖懼,卻不見其怯懦。浮生若幻,立德立言,一個(gè)人臨終前可以拍著胸脯無愧于心地說我這輩子宣傳了許多正能量的文字,揭露了許多丑惡現(xiàn)象而無憾無怨。
梨花繞樹
郭筠婚后隨丈夫曾紀(jì)鴻在北京居住時(shí)已成為名噪京華的才女,后來有《藝芳館詩存》行世。藝芳是郭筠自署的書齋名,取自陸機(jī)《文賦》中“傾群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rùn)”之意。“群言”即諸子百家之言,“六藝”即詩、書、禮、樂、易、春秋。“不用古人句,只用古人意”,兩句話合起來的意思是吸取古人經(jīng)典的精華,如蜜蜂采百花一樣釀出自己的蜜來。郭筠以此命名,表達(dá)了自己讀書學(xué)習(xí)的態(tài)度和方法,即善于棄其糟粕,揚(yáng)其精華,絕不食古不化。
郭筠之詩詞,有抒情即興之作,親友唱和之韻,勖勉兒孫之章,也有憂國(guó)傷時(shí)之作。感情豐富,清新可讀。比如這首:
《故園》
楊柳岑差蕩晚風(fēng),十年又認(rèn)舊簾櫳。方塘水滿秧初綠,別浦春回杏晚紅。處處青山含翠黛,依依簫竹郁蔥蘢。饕餮剪韭香粳熟,戚友相逢酌圃中。
王湘綺先生評(píng):“如彈丸脫手。”
(注:查1993年出版的《雙峰縣志》這首詩的“十年又認(rèn)舊簾櫳”,“又”字處是“歸”字,“依依簫竹郁蔥蘢”,“簫”字處是“松”字。而百度和《雙峰縣志》的一模一樣。2010年出版的趙世榮先生的著作《曾國(guó)藩故園的才女》與2014年出版的胡衛(wèi)平先生的著作《曾國(guó)藩文化世家》的版本如出一轍。想必是后來修改了的,特此說明)
《雪》
向晚嚴(yán)寒侵瘦骨,布衾如水縮雙肩。漸看柳絮撲窗艷,恍若梨花繞樹妍。放眼乾坤嗟白發(fā),滿腔滋淚老青氈。霸陵夜獵無人見,爭(zhēng)似騎驢得自然。
廖泉珠先生評(píng):“一氣呵成,無懈可擊。”
柳絮撲窗,梨花繞樹,一撲一繞畫面感十足,清新脫俗。“恍若梨花繞樹妍”這漫山飛舞的梨花,這晶瑩剔透的白雪不正是郭筠自己?jiǎn)幔咳松喽蹋瑓s要活得灑脫坦然。
郭筠在《記三姊羅夫人事》中,津津樂道地夸贊婆家的姐姐,即曾文正公的三女兒,湘軍之母羅澤南的次媳曾紀(jì)琛。郭筠認(rèn)為閨闈之事,符合一般的道德規(guī)范看起來容易做起來卻很難,如能勤勤懇懇,幾十年而不改變,不爭(zhēng)一日之長(zhǎng),才能比別人略強(qiáng)。郭筠欣賞三姐精女紅,巨細(xì)具諳,善烹飪,又節(jié)儉,“事姑以孝,處姒妹以和,待人恭溫,相夫有禮。”把和婆婆、姐妹、老公、鄰居等關(guān)系都處理好了,侯府的千金在婆家洗衣做飯,打掃廁所,卻沒有怨言。丈夫沉湎于酒,三姐能及時(shí)地拉丈夫到正途,丈夫死后,教撫丈夫的子女,讓子女成才,使家族興旺,晚年樂善好施,尤其對(duì)貧弱者,無論親疏。與愛慕虛榮者的做派是天壤之別。聞名遐邇的三姐曾紀(jì)琛,近七十歲無疾而終,葬之日,遠(yuǎn)近數(shù)十里來送者,都擦著眼淚說:“真是個(gè)賢夫人啊!”真誠的文章是一個(gè)人內(nèi)心世界的折射。郭筠對(duì)夫家的姐姐不吝相惜贊美之情,她自己也是這樣立世做人的,有過之而無不及。
郭筠十三歲喪父,十九歲即在公公曾國(guó)藩的主持下嫁給了曾國(guó)藩的次子時(shí)年十八歲的曾紀(jì)鴻。曾紀(jì)鴻雄毅有大度,著書不倦。他精通數(shù)學(xué),研究起來經(jīng)常不舍晝夜。曾紀(jì)鴻本來身體強(qiáng)健,郭筠與丈夫的關(guān)系和睦融洽。曾紀(jì)鴻每次坐在書桌前演算,郭筠便手持稿紙站在旁邊,眉眼里無不露出欣賞和愛意。曾文正公和歐陽夫人先后逝世,作為兒子的曾紀(jì)鴻悲傷不已,更加沉迷于演算。郭筠愛在眼里疼在心里,讓夫君悠著點(diǎn)兒,身體是第一要緊呀。可是紀(jì)鴻不聽,于是逐步病入膏肓,三十三歲便在北京去世。郭筠肝腸寸斷,幾欲以身相殉。常齋祭,并在夫君墓地前植上松樹和槚樹。年紀(jì)輕輕的郭筠守了寡,面前四子一女皆幼小,挈子離開京師,回到湖南雙峰(時(shí)湘鄉(xiāng))荷葉鄉(xiāng)富厚堂。
(郭筠長(zhǎng)子翰林苑才子曾廣鈞在郭筠60歲的壽頌文《誥封一品夫人曾母郭太夫人事略》有詳細(xì)記述)
富厚堂第一女主人
雙峰縣荷葉鎮(zhèn)地處盆地,汽車在曲曲折折的山路上繞行,何止十八道彎才來到晚清中興大臣曾國(guó)藩的故居富厚堂。富厚堂是我國(guó)保存最完好的最后一座鄉(xiāng)間侯府。荷葉的水池中多種青荷,碧綠的圓葉襯托著粉紅的花朵,煞是清新脫俗。紅色湘軍帥旗矗立在半月荷池畔高高飄揚(yáng),顯現(xiàn)出侯府的威嚴(yán)和壯觀,靈魂都為之一顫。曾經(jīng)大清龍鳳旗也在此迎風(fēng)起舞,與帥旗遙相呼應(yīng)。郭筠的公公曾國(guó)藩除了為其父曾麟書守喪期間在富厚堂后山的思云館居住過外,并沒有在富厚堂居住過,曾國(guó)藩童年少年青年時(shí)期居住了二十六年的故居是離富厚堂十余華里外的白玉堂。
歷來說婆媳是前世的仇人,婆媳關(guān)系處得融洽的是極少的。尤其是歐陽夫人晚年失明后,脾氣暴躁,心中郁悶,有所需要又不直接說,夜起數(shù)次。唯郭筠能夠理解,盡孝。伺候婆婆好幾年。歐陽夫人常對(duì)人感嘆:“吾婦賢若此,吾忘吾貞疾。吾歐陽氏有賢姑婦,侯相為之傳,異日,孰傳吾婦者?”足見婆媳感情非同一般,婆婆對(duì)兒媳的滿意度和贊賞度亦是很高的。
同治十一年(1872)曾國(guó)藩去世后,兩年后,歐陽夫人去世。光緒四年,郭筠的夫兄曾紀(jì)澤攜夫人子女出使英、法、俄等國(guó),一去整整八年,至光緒十二年回國(guó),十六年逝于京師(曾紀(jì)澤光緒三年離開富厚堂,從未回家鄉(xiāng))。光緒七年(1881),曾紀(jì)鴻英年早逝。曾氏子孫幾十人聚居富厚堂,一切家務(wù)皆賴郭筠主持,年輕守寡的郭筠可謂富厚堂第一主人。
如今供游人參觀的富厚堂雕琢得古香古色的房間里擺放各式各樣的舊物,舂米的石碓,犁田的耙滾,紡紗的紡車,揀沙石的米篩,物品的容器斛、盤箕、米筒、斗。品學(xué)兼優(yōu)的郭筠秉承先人遺訓(xùn),曾在這里指點(diǎn)江山,告誡子孫自強(qiáng)自立,不染紈绔習(xí)氣。男女皆應(yīng)知習(xí)一樣手藝,男女皆應(yīng)有獨(dú)自出門的見識(shí),男女皆應(yīng)勤儉,俠義,有大公無私的精神。字?jǐn)?shù)雖然不多,做起來卻不容易。
郭筠四子一女在她的教育和熏陶下都取得了很好的成就。長(zhǎng)子曾廣鈞,年僅23歲中進(jìn)士,是翰林院最年輕的才子,著有《環(huán)天室詩鈔》三冊(cè)行世。次子曾廣镕,花翎二品銜湖北候補(bǔ)道,湖北厘牙局總辦,湖北按察使。三子曾廣銓,秀才,駐英使館參贊、出使韓國(guó)大臣。四子曾廣鐘,浙江候補(bǔ)道,有《余姚地方田畝升科書》《新舊約圣經(jīng)提要偈子》等書行世。女兒曾廣珊,是俞大維的母親,詩文書法俱工,有《鬘華仙館詩鈔》行世。
曾紀(jì)鴻去世時(shí),長(zhǎng)子曾廣鈞才十五歲,次子曾廣鐘才六歲,雖是官宦之家,但時(shí)逢亂世,又是年輕的寡母,撫養(yǎng)且不易,教育的難度不可謂不大。何況是把兒女五人都教育成才。長(zhǎng)子曾廣鈞說自己的母親教育子女是“嚴(yán)而惠。治家有法度,諄諄訓(xùn)誨不遺。微賤,或有驕慢者,不遽責(zé),導(dǎo)之以禮,六自將畏。奢汰者,示之以節(jié),人初免為之,久而安之。”自古慈母出敗家子多,嚴(yán)格而仁愛,才是眼光高遠(yuǎn)的教養(yǎng)方式。“嚴(yán)而惠”與美國(guó)的教育專家、《正面管教》的作者簡(jiǎn)·尼爾森的教育理念“溫柔而堅(jiān)定”有異曲同工之妙。孩子一開始不能適應(yīng)這種嚴(yán)苛的規(guī)則,久而久之,就成習(xí)慣了。
郭筠高瞻遠(yuǎn)矚,親課兒曹,對(duì)于孫輩的影響應(yīng)該說是更大的。郭筠的孫女曾寶蓀女士曾回憶:“蓋吾等對(duì)國(guó)家如有貢獻(xiàn),悉藝芳老人所賜也。”她在《藝芳館詩存· 前言》中說:“先祖母高瞻遠(yuǎn)矚,在光緒末年已知國(guó)內(nèi)政治勢(shì)趨鼎革,而學(xué)術(shù)演進(jìn),偏重科學(xué),陳長(zhǎng)孫女早適姚氏外,其余三房男女孫輩,均令其遠(yuǎn)赴英美學(xué)習(xí)科學(xué)。”
1918年至1949年,曾寶蓀與堂弟曾約農(nóng)在長(zhǎng)沙創(chuàng)辦藝芳女校,以紀(jì)念祖母對(duì)自己“甘聿之教”。姐弟分別擔(dān)任校長(zhǎng)和教導(dǎo)主任。
郭筠未成年即博覽群書,尤其好詩,能背誦千余篇,寫詩數(shù)百篇。晚年喜歡看翻譯的書和報(bào)紙。并敦促子孫:“時(shí)局日迫,若盡通舊學(xué),即無暇治西文,中學(xué)半之,西學(xué)半之,可也。”博古通今,學(xué)貫中西,無不體現(xiàn)出郭筠與時(shí)俱進(jìn)的思想。
昔日孟母三遷,子不學(xué),斷機(jī)杼;子發(fā)之母,刺子驕泰,將軍稻粱,士卒菽粒,責(zé)以無禮,不得人力;齊田稷母,廉潔正直,責(zé)子受金,以為不德,忠孝之事,盡財(cái)竭力。孟母勸子勤學(xué),子發(fā)母教子無私,田稷母教子清廉。不正是郭筠手書的《富厚堂日程》六條要求的嗎?不正是富厚堂堂前門聯(lián)“清芬世守,盛德日新”?古為今用,所以說郭筠是曾國(guó)藩家教思想的具體實(shí)施者一點(diǎn)也沒錯(cuò)。一家行之,一鄉(xiāng)風(fēng)化,則強(qiáng)國(guó)之根矣。
富厚堂的風(fēng)
荷葉原無栽種棉花茶葉的先例,郭筠嘗試種,后形成風(fēng)氣。蓮花、小麥也都自己試種。空暇的時(shí)候則種蘭花菊花牡丹等名卉自娛自樂。給一小園圃稱為“藝芳館”。
郭筠平時(shí)節(jié)儉,但是賑災(zāi)和對(duì)家塾,則不惜重金。光緒十一年(1885),直東大災(zāi),捐出千金。平常的,如助育嬰,助團(tuán)練,助水旱數(shù)百金,則不勝枚舉。
晚年的郭筠仍是黑發(fā)如云,白發(fā)找不出幾根。郭筠勤奮好學(xué),深究醫(yī)理,不僅自醫(yī),還給家人、小孩看病。大家吃了她的方子病就好了。二十多年,家里沒有受困于藥物。郭筠晚年無多憂患,頤情養(yǎng)年,唯國(guó)勢(shì)不振,世局艱難,時(shí)常感慨。因?yàn)樗赃^國(guó)運(yùn)不濟(jì)、百姓艱難的苦。與堂弟媳劉鑒及女兒曾廣珊新詩唱和,多有憂心國(guó)事之句。
富厚堂的家風(fēng)家教由郭筠散播開來,吹遍了荷葉,吹遍了雙峰,吹到了全國(guó)的各個(gè)角落,吹了一百多年了。
作者簡(jiǎn)介:胡曉霞,婁底市作協(xié)會(huì)員。出版散文集《芬芳的流年》。
責(zé)編:扶雄芳
一審:鐘鼎文
二審:熊敏
三審:羅曦
來源:冷水江市融媒體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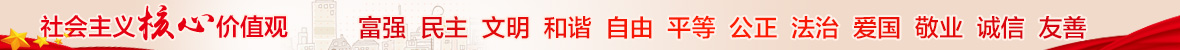
!/ignore-error/1&pid=45434035)
!/ignore-error/1&pid=14055395)
!/ignore-error/1&pid=50436665)
!/ignore-error/1&pid=469166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