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景三帖(散文)——謝新茂
風景三帖
謝新茂
渠江源
渠江源傳為渠江之源。渠江最初的涓流從云層之上的山巔叮叮咚咚破石而出,順著陡峭的茶溪谷或瀉而為瀑,或嘩然為流,一路匯聚更多峽谷溝壑竄出的山溪,由高到低向北轟然流去,高歌猛進五十里后,注入資江。
夫江之源者,多為山之至高、人跡杳然之地。渠江源自不例外。群峰如浪,四面八方前呼后擁呼嘯而來,層層疊疊把渠江源的大山推至更高處。滔天巨浪縫隙中卷起的大風,吹皺了路,吹散了云,也吹瘦了渠江源人的希望。
此地有人過日子?有。瑤人屋場若有卻還無,那是一縷歷史的青煙,訴說當年瑤人生活的生動場景。后來瑤人走了,漢人來了,搭起了木板房,開出了瘦如荊棘的梯土,把日子過將起來。然而此地離天近,月亮大如斗,手可摘星辰,只宜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仙居住。凡人居住,卻是離地更遠,從稍平整一點的地方上山,兩三個時辰還在山肚子里打轉轉。這山望著那山,有雞鳴,有狗吠,有鳥獸蟲魚之響,就是不見人影。山很陡,地很薄,山里人的苦逼日子,幾百年,上千年,過得就如搖搖欲墜的木板房,黑不溜秋的,說不定什么時候就散了架。
幸好可種茶。
渠江源種茶的歷史有多久?一個專司茶道的小姐姐將我帶至一株高可盈丈的茶樹旁,告訴我,這株茶樹,已經四百多年風雨。樹身斑駁,冠蓋如云,其枝如爪,其葉如墨。然而幾十年前,這里是沒有大規模種茶的。此地位于大山之中,黃鶴之飛尚不得過,猿猱欲度愁攀援,在交通閉塞、物流不發達的當年,陡峭的山坡上開的那點梯田梯土,人不哄地皮,地也會哄肚皮,出產的玉米高粱紅薯,做成糊糊能夠把肚子填飽就已心滿意足,根本騰不出多余的地來種植茶葉這種高雅之物。那時候種茶,只是懸崖峭壁山旮旯邊的點綴,讓山里人清苦的日子,沉浸一點茶水的幽香。渠江可以嘩嘩流向山外的繁華之地,渠江源人卻只能固守茫茫群山中的高山之巔,與大山語,與天人語,卻無法與山外的世界語。
直至隆平一出天下飽,這里方有大規模種茶之舉。
此處山土不肥不膩,山嵐霧靄早晚浸染,陽光吹彈可破,正是適合種茶之處。當年不知是誰,在春天的某一天早上醒來,將原來種玉米高粱紅薯的土地翻了,種上了第一株茶樹。然后猶如一夜春風來,千棵萬棵茶樹栽。稍微平整一點的山腰上,昔日的糧食作物飄帶,不時之間換成了一條條嫩綠、碧綠、墨綠輪流轉換的茶葉樹飄帶。
我們去渠江源的時候,已是深冬,橘黃色的陽光夢幻一般籠罩著散發著茶葉酥香的山村。在陽光漫布的山坡上,村民們正在茶業公司組織下,給茶樹施肥。茶園正如墨綠的壁掛,在山坡上流淌,在墨綠的縫隙里,透露出土地的泥黃。那些山民就隱約在墨綠與泥黃之間,在每一株茶樹旁,挖好淺淺的肥坑,然后施上黑色的肥料,小心覆蓋好,等待一場春雨后,孕育出嫩綠的新芽。
茶園溫潤了山民的生活,但山民們依然需要手握鋤頭,肩扛箢箕,一點一點去開墾自己的幸福。第二天早上雞鳴三更之時,我們還縮在溫暖的被窩里睡得正香,他們已經匆匆吃過早餐,一頭撲進了茶林,讓自己與早上清麗的天空、與明凈的陸羽廣場相依相融,成為渠江源最美的風景。
直到中午時分,他們才下山,在茶葉公司碩大的食堂里安靜地匆匆吃飯。伙食很好。茶農們的鞋上、褲管上,沾滿了茶園里新鮮的泥土,眉毛上、頭發上,依稀還有晶瑩的露珠,而神態全部安詳得如同冬天里溫暖通透的陽光。這是對生活心滿意足透露出來的安詳。茶園如畫,生活如畫。短短幾十年,他們的生活經歷了貧窮與富足的霄壤之別。他們享受并珍惜著眼前美好的日子。吃過飯后,他們在院落里走走,抽一支煙,復又上山,繼續勞動,直到暮色四合。
一個四十左右的漢子告訴我,茶園里最美麗的時光,是春上采茶季節。春雨澆灌,春風吹拂,茶樹新抽的葉芽,最初含苞的那一刻是橙紅,接著是鵝黃、是嫩綠、是翠綠,站在茶園里靜靜地注視著它們,那些層次分明的綠在云霧中不斷洇染,讓人恍然覺得,那是綠色的火焰在舞蹈。采茶的人在綠色的火焰中穿行,猶如蝴蝶翻飛。
盛裝的采茶姑娘在綠色的茶園里一邊采茶,一邊歌唱,該是多么迷人的一幅畫面!然而,他接下來告訴我,采春茶,緊張得飯都沒時間吃。最好的春茶,是一芽苞一葉片,其次是一芽苞兩葉片。三葉片、四葉片,那就是非常普通的茶了。而新茶由上一級長成下一級,往往只有一兩天時間。為了新茶在剛剛呈現最好的品質時采回來,采茶堪比一場激烈的戰斗。他們既沒有時間去欣賞茶園的風景,也沒有時間,去唱一曲采茶歌。
被層層大山推至近天的渠江源,因為遠離人間,所以風景獨異。然而,這種獨異只是我們的體驗。當我們住進剛剛建好的含遠山、吞云霧的世外山居,住進仿古木板房建筑的紫金山莊,我們盡可以贊嘆眼前與山外獨異的風景。但是,這些風景對生活在渠江源的山民們來說,就是他們勞動的背景。他們感激生活饋贈于他們茶園,饋贈于他們雖然陡峭狹窄卻通行無阻的盤山公路,饋贈于他們生活中需要的一切,然后用自己畢生的精力,將他們身處的風景描摹得更美麗。
他們只是描摹風景的人。他們不唱茶歌,只是將茶歌飛到山外,讓那些熱愛喝茶的人,沉浸在紅茶綠茶泡出的美好畫面之中。
龍居崖
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田家者,冷水江三尖龍居崖也。此地有崇山峻嶺拔谷而起,有茂林修竹連綿起伏,有玉帶小溪或飛瀑而下,或環山響叮當。有五六墨墨黑木板屋雜立濃郁之樹陰下,有三五群雞鴨鵝引吭高歌藍天白云之間,有白狗黃狗數只搖尾乞憐于主人客人腳旁。
卻沒有田。
既謂田家,為何無田?此地當年是有田的。村落懸在半山腰上,當年伴著那些木板屋的興建,屋前屋后的山旮旯里,祖先們用鐵鍬鐵錘鐵鋤頭、鐵手鐵腳鐵肩膀,開出了三兩塊稻田旱土,就在這里扎下了根。這些梯田旱土,看天吃飯,不看人吃飯。土地瘠,山民更瘠。前幾年政府搞搬遷,此地山民久旱逢甘霖,全搬遷去了人煙稠密處、經濟發達處。故人已乘黃鶴去,此處空余木板房。有好事者懷思舊之悠情,將人去樓空之木板房全盤了下來,整舊如舊又整舊如新,立庖廚,立旅舍,立茶館,又借飛瀑流泉,山石松林,做游人閑暇之休閑去處。其龍居崖水寨之名頭,日漸響亮。
名為水寨,自然少不了水。高山有好水。此地山高,其水自山頂轟然而下,雖為細流,卻有非常之氣,其飛珠濺玉之勢,力壓鼎沸之游人驚呼聲。加之我等初來乍到,茫然不知水之來處,聽主人稱此水為龍口吐珠,也就更加敬畏。飛湍而下之后,積為深潭。潭水清悠,在此處休整之后,慢悠悠沿著水渠,從容而流。水渠繞著山轉,或寬或窄,或陰或明;流水伴著鳥語,鳥語有婉轉之氣,水流有生物之靈。水渠分兩邊。里邊是前人修的,或三合土,或鑿石為磚,上生苔癬,先人的足跡神采從中悠悠吐出來。外邊是時人整的,一色的水泥。前人的付出與時人的付出,涇渭分明又混為一體。
不管前人還是今人,人類改造世界的夢想,是亙古不變的。
人類越想改變世界,創造的嶄新器具就越多,淘汰并成為古董的物件就越多。比如,汽車火車飛機出現了,轎子成了古董;收割機出現了,鐮刀成了古董。倘若有人還死守著古董做事,那做事之人更會被譏為古董。
器具成為古董讓人懷念,它反襯的是人類孜孜追求的進步;人成為古董被人譏笑,它比證的是人的抱殘守缺。
水寨的主人許是深刻地體察到這一點的。山寨木板屋的外墻上,精心地布置著斗笠、蓑衣、鐮刀、鋤頭、犁耙等農耕器具,山寨的空坪里,擺放著打稻機、扮桶、水車等用品。走進山寨,年過半百如我者,仿佛走進了自己少年時代的鄉村。
這些掛在墻上、擺在空地里的農具,伴隨著出身農家的我走過整個少年時光。赤日炎炎似火燒。野田禾苗半枯焦。赤日炎炎之下,我用瘦小的身軀握著它們、扛著它們,在田野里奔跑。它們的手柄上,浸潤著我帶著咸味的汗水;那些鐮刀口、鋤頭尖,還留有我少年的血跡。一晃四十年,現在再見到它們,一股久違的親切感涌上心頭。
然而這種親切感,只是一個與它們有過親密接觸,但又早早離開了它們的人才會有的親切感。我的父輩、祖輩、祖輩的祖輩,一輩子都與它們打交道,更多的只有痛苦的記憶。農夫心內如湯煮,公子王孫把扇搖。他們整天都在用湯煮心,沒有功夫來發思古之悠情。而我在城市出生長大的后輩,更不可能與之產生親切感。在他們的眼里,這些曾經養活我們無數代人的器具,已經成為單純的古董。鐮刀、鋤頭、箢箕,他們沒有握過;打稻機,他們沒有踩過;籮筐,他們沒有挑過。他們已想象不出,這些器具曾經是每個中國人的生命所系。當我輩目指每一件器具,充滿深情地告訴后輩是什么東西做何用途時,后輩的反應也許是一臉的茫然:“哦,鐮刀。”“哦,鋤頭。”然后,就把臉別在一邊,去欣賞他們感興趣的東西。
有更新的器具在等待著他們。
但這些古董依然讓我欣慰。它們中的每一項成為古董,就證明有一種更先進的器具代替了它。而每一項嶄新的器具,就是人類的一次進步。
古董越多,人類就越進步。
龍居崖水寨的每一個地方,布滿了我們曾經非常熟悉的農具,它們交織著舊與新的時空,讓我體味著已經遠逝的少年歡樂時光,更讓我體味到了時代前進的踏踏腳步。
故人者,我當年在冷水江謀生時的文友也。他們有新朋友,更多是我年輕時的舊相識。我與他們的友誼,也已穿越時空,愈久彌新。
萬樂村
萬樂村在婁底北郊,距城區十來公里。挪一下腳,即能到達。村后有山,名烏石峰,山峰層層疊疊波浪一般擁上去,堆青疊翠,傳為南岳衡山七十二峰之一。它還有另一個身份,就是婁星區境內最高峰,萬民仰止。有諸天殿建于近山頂之處。諸天殿聽上去就大氣。諸位天上神仙,在此集合,快趕上玉皇大帝凌霄寶殿的地位了。環山皆平疇。立于峰頂,左右前后極目遠望,東邊日出西邊雨,盡收眼底,仿佛天下風景,全入胸襟。更有涼風入懷,衣袂隨之飄然,如我之大腹便便者,也覺如神仙般飄飄欲仙,更不用說苗條俊俏如你者,立于此處,就是玉樹臨風,讓天下人傾倒。
鄉親多年以耕作為業。其美麗田疇,鏡面也似,在村子前面鋪展開來。綠波蕩漾的水庫,在田野一側做著忠誠的護花使者。想當年禾苗綠了,麥苗綠了,稻子黃了,麥子黃了,在眼前由近及遠錯落有致地鋪展著,應是極可觀賞的。但當年的稻和麥,是用來飽肚的。鄉親們一天到晚撅著屁股,繡花也似種著這些地,肚子卻依然餓著,衣衫也依然襤褸著,再好的風景,也沒心思觀賞。好在這個村的鄉親,有一個絕技,就是架高壓線。農民不懂高壓電,農民會牽高壓線。他們全國各地來回跑著,在荒山野嶺或者城市,“嘿哧嘿哧”將高壓電桿一根根樹起來,“嗚呼哎喲”將一根根拇指粗的電線拉起來。一身臭汗之后,也將自己的腰包鼓了起來。
有錢了,那村后的烏石峰,那世世代代的祖居地,就成風景了。眼里有了風景,心里更有了風景。他們就按照心里的風景,好生打造起來。平整的鄉村公路,鋪起來了。公路兩旁一水的桂花樹。在農歷八九月里,空氣里密密麻麻的,全是桂花的香味。公路近旁的田野里山嶺邊,春有桃花李花、油菜花芍藥花,秋有格桑花,冬有臘梅開。格桑花開紅艷艷,千家萬戶幸福來,精致的農居在花海之中建起來了。一水的白墻紅頂,或者白墻藍頂,掩映在綠意盎然的風景樹中,安靜得沒有炊煙,只有雞鴨的啼叫和鳥的啁啾。水庫邊建起了水泥臺階,直通水面,一根釣桿,一蓑煙雨任平生。村子中間建起的廣場,更是花的海,樹的洋,條凳掛籃擺四方。雖然比不得城里的公園大氣,但比城里的公園空氣好,吸一口,全是甜的。是三百年楓葉的甜,是鳥兒鳴雞兒叫的甜。當然啦,那烏石峰上的諸天殿,更得大手筆重建。得讓神仙來這兒住得舒適,讓神仙天天呆在這兒舍不得走,保佑著鄉親歲歲平安,讓這方水土,得到神仙的格外眷顧。
成了風景,來看風景的人,就多了起來。到了周末,附近城里的人稍稍挪一下腳,就來到了萬樂。“中國萬樂”,一萬個“樂”,總有一“樂”適合城里人的胃口。愛花的,看花吧;愛香的,聞香吧;愛釣魚的,垂釣吧;什么都不愛的,爬山吧,找個農家樂小酌吧。他們要什么,都能給,關鍵是放松心情。
忽然有一天,我來到了這里,中國萬樂。甫走下車,撲入眼簾的,是美麗的芍藥花;撲入鼻中的,是春天花的濃香;吸入肺腑的,是清甜的空氣。不多的時間,鄉村初夏的微涼慢慢地從皮膚,沁到肌肉,沁到骨頭,全身從里到外,竟有被水洗一般的感覺。身子輕了,心也輕了。天空有多高,我的心就有多高;烏石峰有多青翠,我的心就有多青翠。整個的人,在清涼季節里,全融化在這美好的風景之中了。
而更美好的,是他們那一張張純潔的笑臉。來到村里,看到的每一個村民,都是笑靨如花。來者都是客,笑臉相迎送。讓我覺得,我和他們,早就是熟悉的人。這里不賣紀念品,這里只有農家菜。當我們欣賞完風景,來到一家農家樂,那送入口中的飯菜,就是我回到農村老家時吃著的飯菜,香,甜,辣,吃完了,還想吃。
它讓我想起了兒時的味道,它讓我記起了鄉村的味道。它讓我渾然覺得,我就應該到農村去,做一個自在的農民,在藍天白云之下,享清野閑人之樂也。
作者簡介:謝新茂,湖南省作家協會會員。先后在《散文》《散文百家》《散文天地》《美文》《湖南文學》《人民日報》等報刊發表作品若干,多篇作品入選、獲獎。出版《落英繽紛》《不要問我從哪里來》《風景中的故鄉》等。
責編:扶雄芳
一審:鐘鼎文
二審:熊敏
三審:羅曦
來源:冷水江市融媒體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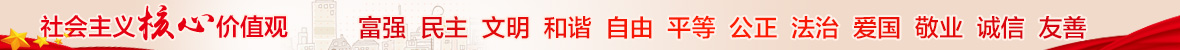
!/ignore-error/1&pid=45434035)
!/ignore-error/1&pid=14055395)
!/ignore-error/1&pid=50436665)
!/ignore-error/1&pid=46916695)